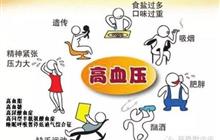医疗事故 降血压过快导致脑梗塞加重 |
| 分类:案例集锦 时间:(2019-11-12 10:42) 点击:292 |
医疗事故 降血压过快导致脑梗塞加重
1, 2015年5月21日 22:24 阅读 2 新浪博客 因“突发头昏10小时”于2011年4月29日入住军区总院神经内科,病历记载XX既往高血压病史10年,最高血压150/80mmHg,平素规律服用络和喜,血压控制良好,2005年曾因“左肾透明细胞癌”接受手术治疗。入院查体时XX神志清楚,语言流利,右侧眼睑较左侧稍下垂,右侧面部无汗,左侧面部有汗,四肢肌力、肌张力正常,双下肢跟膝胫反射差,初步诊断为短暂性脑缺血发作、高血压病1级。入院后军区总院给予XX检测血压、活血化瘀、清除氧自由基、抗血小板等治疗。MRI检查显示XX双侧基底节区、侧脑室旁及脑干多发缺血灶;MRA检查显示XX脑动脉硬化,右侧大脑前动脉、左侧大脑前动脉A1段狭窄。同年5月3日军区总院给予XX加用培哚普利片降压治疗。同年5月5日凌晨XX出现左侧肢体无力现象(无病程记录),军区总院上午给予XX奥扎格雷、乙酰谷酰胺等治疗,嘱查头颅MRI。当日下午XX接受MRI检查,显示脑桥急性脑梗塞,军区总院仍继续给予XX使用培哚普利片。在同年5月7日查体显示XX左侧鼻唇沟浅,左上肢肌力3级、左下肢肌力4级,走路不稳,症状加重的情况下,军区总院给予XX依达拉奉、维生素B6、高压氧等治疗。后XX病情渐稳定,于同年5月23日出院,军区总院嘱康复治疗。当日XX转入,,省人民医院继续治疗,于同年7月29日出院,出院时生活基本自理,能独立行走,左上肌力4级,左下肌力4级。 案件审理过程中,XX申请对军区总院涉案医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如存在医疗过错,医疗过错行为与医疗损害后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医疗过错行为在医疗损害后果中的原因力大小及医疗损害后果、伤残等级等事项进行医疗损害鉴定。 经法院委托,XX医学会于2012年5月30日出具医疗损害鉴定书。鉴定书分析意见为:“根据法院提供的病历资料及现场调查分析,患者‘短暂性脑缺血发作、高血压病1级’诊断明确,医方予活血化瘀、清除氧自由基、抗血小板等治疗符合诊疗常规。患者入院后查MRI及MRA提示颅内多发性缺血性改变、颅内多发脑动脉硬化,血压基本在正常范围之内,医方于5月3日加用‘培哚普利’降压,可加重脑血流低灌注。5月5日凌晨患者发生病情变化后,医方当日无病程记录,对患者病情重视不足,在不能及时查头颅MRI时,处理措施欠积极;在行头颅MRI明确诊断为桥脑急性脑梗塞后,仍使用降压药,不符合诊疗常规。医方未尽合理的诊疗义务,存在医疗过错,与患者脑梗塞进行性加重存在因果关系。患者存在高血压病、脑动脉硬化,是其发生脑梗塞的病理基础,也是目前左侧肢体偏瘫的重要因素。”结论为:“医方存在医疗过错行为,医疗过错行为是患者损害后果的同等因素。参照《医疗事故分级标准(试行)》,患者伤残等级为八级。” XX医学会于2012年5月30日出具医疗损害鉴定书后,XX申请对其护理期限、护理级别、护理人数进行鉴定。法院委托XX医科大学司法鉴定所进行鉴定,XX医科大学司法鉴定所于2012年11月12日出具鉴定意见书认为:“本次法医学检查见其左侧肢体偏瘫,左上肢肌力IV级,左手握力III级,左下肢肌力IV级,左侧肢体腱反射亢进;送检影像片示脑桥脑梗塞灶,双侧基底节区、侧脑室旁及脑干多发缺血灶,脑动脉粥样硬化;结合治疗经过、影像片及本次检查所见,根据G/T800-2008《人身损害护理依赖程度评定》第4.1.2条、第4.2.2.1条之规定,XX目前状况存在部分护理依赖,其伤后住院期间及出院后需1人长期护理。” 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规定,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伤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XX入院后经检查显示颅内多发性缺血性改变、颅内多发脑动脉硬化,血压基本在正常范围之内。军区总院于2011年5月3日给予XX加用“培哚普利”降压,该医疗方法可加重脑血流低灌注,故军区总院对于该医疗方法可能对XX产生的医疗后果应谨慎监控。但在2011年5月5日凌晨XX发生病情变化后,军区总院对XX病情重视不足,处理措施欠积极。后在明确诊断XX为桥脑急性脑梗塞后,军区总院仍给予XX使用降压药,不符合诊疗常规,未尽到合理的诊疗义务,存在医疗过错,军区总院的诊疗行为与患者脑梗塞进行性加重存在因果关系,根据XX医学会出具的医疗损害鉴定结论,法院认定军区总院对于XX医疗损害后果承担百分之五十的赔偿责任。 判决:中国人民解放军XX军区XX总医院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XX医疗费51474元、护理费13072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837元、残疾赔偿金51365元、精神损害抚慰金7500元,共计241896元。 2, 医疗事故 降血压过快导致脑梗塞加重最后死亡 2015-06-29 00:06 阅读 0 患者丰某,1968年8月11日生,生前系,,教育学院职工。因“咳嗽、咽痒3天”,丰某于2011年1月26日21:50至,,省人民医院急诊就诊,查血常规示:白细胞11.6×109/L、中性粒细胞94%,诊断:上感,予头孢匹胺抗感染治疗。1月27日患者因心悸气短再次急诊就诊,查体:心率快,律齐,查心电图示:窦性心动过速,左室肥大伴继发性ST-T改变,至心内科门诊就诊,查体:心率120次/分,心律齐,主动脉瓣区第二心音增强,血压220/150mmHg,诊断:高血压病、高血压急症,建议住院进一步诊治,患者拒绝,予口服降压药治疗,转至急诊科,予静滴硝酸甘油降压治疗。13:50时患者血压210/140mmHg,改用压宁定降压治疗。17:09患者血压179/129mmHg,18:08血压170/110mmHg,予压氏达口服。21:00查头颅CT示:多发性脑梗塞。1月28日3:35患者血压133/96mmHg,继予压定宁100mmHg降压治疗。9:22患者住入心血管内科,初步诊断:高血压病因待查,肺部感染?,多发性脑梗塞。急查WBC8.3x109/L,N91.1%,Cr288.8umol/L,入院后予降压、补钾、抗感染等治疗。当晚22:00患者出现神志模糊,胡言乱语,出汗多,血压106/78mmHg,血氧饱和度91%,双侧瞳孔等大等圆,对光反射灵敏,两肺呼吸音稍粗,右肺可闻及少许低调干啰音,测血糖示14mmol/L。神经内科会诊,予抗凝、醒脑等治疗。当夜检测心率、血压、呼吸及血氧饱和度。1月29日晨查房时患者呼之不应,心电监护示:心率80次/分,呼吸30次/分,血氧饱和度80%左右,血压80-100/50-70mmHg,查血气分析示氧分压59mmHg,请呼吸内科、神经内科、ICU会诊,行气管插管、呼吸机辅助呼吸及升压、扩容、抗感染等治疗。当日血生化报告示:谷丙转氨酶2989.8U/L、谷草转氨酶5343.6U/L、肌酐479.3Umol/L。患者仍昏迷,转入老年科ICU病区继续诊治。患者多脏器功能衰竭,经治无效,于2月13日19:47时死亡。丰XX、丰先生、张女士系患者丰某第一顺序继承人,丰XX系丰某之子,丰先生系丰某之父、张女士系丰某之母。 2011年3月30日丰XX、丰先生、张女士诉至法院,请求判决:,,省人民医院赔偿总损失医疗费120264.66元、死亡赔偿金593540(29677×20)元、丧葬费25640(51279÷2)元、被抚养人生活费47062.5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元,共计886507.16元的70%,即620555.01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审理中,经丰XX、丰先生、张女士申请,一审法院委托南京医学会对本案进行医疗损害鉴定。 医疗损害鉴定书认为:患者血压显著增高,医方降压药物使用符合治疗原则,但收住入院后对患者综合病情认识不足,降压控制标准偏低,在患者1月28日22时出现意识障碍、血氧饱和度低后,处理措施欠积极,观察病情不全面,存在医疗过错。患者昏迷系脑缺氧缺血及代谢因素所致,与低氧血症、肝肾功能损伤、脑灌注不足等有关。患者入院前存在高血压病、肺部感染、多发性脑梗塞、肝肾功能损伤等疾病,自身病情复杂,进展迅速,是其最终死于多脏器功能衰竭的根本因素。综上所述,医方存在医疗过错行为,医疗过错行为是患者死亡后果的轻微因素。 因丰XX、丰先生、张女士不服南京医学会的医疗损害鉴定并申请重新鉴定,一审法院委托,,省医学会进行医疗损害鉴定。该医疗损害意见书认为:患者因心悸、气短到,,省人民医院就诊,1月27日就诊时BP220/250mmHg,医方给予降压处理并在急诊观察,留观过程中出现双下肢乏力,查头颅CT示:多发性脑梗塞。28日9时许收住院,给予降压、补钾、心电监护等处理,当晚22时患者神志模糊,BP106/78mmHg。29日7时30分患者自主呼吸消失,予机械通气。转入ICU,2月13日患者去世。医方诊疗过程中存在的过错行为:1、1月26日、27日两次急诊对于“上感”患者未检查记录生命体征(体温、血压等); 2、根据血常规结果诊断“上感”,一次性应用抗生素,无延续性处理,不符合抗生素使用规范; 3、患者高血压急症入院,首次测血压220/150mmHg,既往病史不详,根据《内科学》第七版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第262页,“高血压急症短时间内血压急剧下降,有可能使重要器官的血流灌注明显减少,应采取逐步控制性降压,即开始的24小时内将压降至20%-25%,48小时内血压不低于160/100mmHg.”医方降压过快可以导致多脏器损害; 4、收住院后患者病情急转直下,医方未及时报病重(病危);护理记录与监测记录有出入,如同一时间点,记载出现不同的血压值; 6、医方对病情的危重性认识不足,虽有几次讨论,但内容空洞,没有提出针对性的得力措施; 7、对于死因不明病例,没有书面建议尸检。但本病例仍存在较多疑难复杂之处: 1、快速降压,脑动脉供血不足,由于近心端和远心端供血的差异,会导致分水岭梗塞,但该患者头颅CT没有发现典型的分水岭样梗塞,且复查的CT结果显梗塞病情并未进展; 2、患者既往病史不详,入院时心电图提示左室肥大继发ST-T改变,28日肌酐288umol/L(27日生化检查资料缺失),说明患者原有靶器官损害,但随后肝功能损害如此迅速,不能单纯用降压导致灌注不足来解释; 3、因缺少更详细的资料,患者是否存在其他未知的感染源,基于当时当地医疗水平而不能发现,也是值得考量的。 综上,医方在治疗过程中,疏于观察,血压调整过快,早期对感染不够重视,未能及时调整治疗方案,与患者死亡有一定因果关系。医方存在的过错行为与患者死亡存在一定因果关系,其原因力大小为同等因素。 后双方就,,省医学会的医疗损害鉴定书提出问题,要求鉴定人书面答复,,,省医学会复函:1、鉴定确认医方降压过快引起重要器官的损害;降压过快导致重要器官损害与患者死亡有关;本病例属于疑难复杂病例,鉴于病情的复杂性加上患者原有肝肾功能损害,专家酌定原因力大小为同等因素。 丰XX、丰先生、张女士主张的医疗费损失包括门诊急诊检查费、医药费1713.3元,单位未报销医药费88707.36元,医院要求患者自行购买的白蛋白、球蛋白费用29844元。,,省人民医院认可门诊急诊检查费、医药费为1713.3元,单位未报销医药费为88707.36元。对于患者自行购买的白蛋白、球蛋白费用29844元,其中有一笔7200元的票据上的姓名不是患者,也不是患者亲属,故医方不认可该7200元,认可其余的自购白蛋白、球蛋白费用。丰XX、丰先生、张女士主张的死亡赔偿金标准为593540(29677×20)元、丧葬费为25640(51279÷2)元,医方予以确认。丰XX、丰先生、张女士主张被抚养人生活费47062.5(18825元/年×5年÷2)元,认为患者之子丰XX在患者去世时正在上高三,现在正在读大学,应以18825元的标准按五年计算。医方认为患者死亡时,丰XX17周岁,只认可一年的生活费18825÷2=9412.5元。对于丰XX、丰先生、张女士主张的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元,医方认为:患者的基础疾病属重要因素,医方的原因力比例不超过50%,故精神损害抚慰金不应超过25000元。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医疗损害责任纠纷,医疗损害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为医疗过失、损害后果、因果关系。综合本案证据分析,,,省人民医院在对患者的诊疗过程中存在降压控制标准偏低、降压过快、早期对感染不够重视、处理措施欠积极、观察病情不全面等过错。护理记录与监测记录有出入,如在同一时间点记载出现不同的血压值,对此应推定医方存在过错。以上医疗过错与损害后果之间存在相当因果关系。但本病例属于疑难复杂病例,在考虑患者原有肝肾功能损害的同时,还应注意到以下鉴定意见:患者丰某头颅CT没有发现典型的分水岭样梗塞,且复查的CT结果显梗塞病情并未进展,与快速降压所致的通常规律不符;患者既往病史不详,入院时患者原有靶器官损害,但随后肝功能损害迅速,不能单纯用降压导致灌注不足予以解释;患者是否存在其他未知的感染源,基于当时的医疗水平而不能发现。综上,本案的侵权责任比例应综合过错与原因力因素加以考量,酌定医方对患者的损害后果应承担50%的赔偿责任。 关于本案的赔偿范围,医疗费损失应包括门诊急诊检查费、医药费1713.3元,单位未报销医药费88707.36元,自购白蛋白、球蛋白费用29844元(从治疗的连续性判断,对于其中他人代购的7200元亦予认定)。死亡赔偿金593540元、丧葬费25640元应当纳入损失。被抚养人生活费应计至丰XX成年,按一年的标准计取9412.5元。以上纳入赔偿范围的赔偿总额为748857.16元,50%的份额应为374428.58元。考虑到医方的过失性质和程度以及患方的精神痛苦,酌定精神抚慰金为25000元。综上,医方应赔偿费用合计为399428.58元。对于患方的其他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之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省人民医院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丰XX、丰先生、张女士399428.58元。二、驳回丰XX、丰先生、张女士的其他诉讼请求。 宣判后,,,省人民医院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并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判决所依据的鉴定结论不具有合法性。1、一审法院委托南京市医学会鉴定,并依法出具医疗损害鉴定书,在被上诉人无合理理由情况下,又委托,,省医学会进行鉴定,不符合法律规定。2、,,省医学会出具医疗损害鉴定书后,上诉人质询,,,省医学会未经合议,直接作出“三句话”的草率意见。3、,,省医学会鉴定人未能出庭接受质询,侵犯上诉人的诉讼权利。4、一审法院采信,,省医学会医疗损害鉴定结论、否定南京市医学会的医疗损害鉴定结论,但未就此作出评价。本案应采信南京市医学会鉴定意见。二、一审法院未能查明案件事实。1、针对,,省医学会医疗损害鉴定结论,上诉人提出十项质询意见,,,省医学会未能作出合理解释。2、1月28日病程记录患者血压为105/70mmHg,内科护理记录血压为106/78mmHg,两份记录是医护人员分别测量的即时血压,并作出合理解释,一审法院直接推定上诉人存在过错没有事实依据。3、该案发生在2011年,,,省医学会的鉴定依据是《内科学》第七版(2008年版),而本案应当适用《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2010》的规定。4、,,省医学会未就因果关系详细说理,而直接作出了存在一定因果关系、原因力大小为同等因素的既相互矛盾、又无相应依据的结论。 丰XX、丰先生、张女士答辩称:一、,,省高级人民法院相关文件规定,一审法院如果认为确需重新鉴定,可以委托,,省医学会进行鉴定。关于专家质询,如果鉴定专家确实无法到庭接受质询的,可以出具书面意见,省医学会书面答复内容非常清楚,不存在违法。一审法院采纳,,省医学会鉴定结论,是综合所有证据材料以及两级医学会的鉴定报告依法作出判断,符合法律规定。二、对于医疗事实,患方一直有意见,但该案已经持续3年,故没有提出上诉。医院病历存在明显造假,导致相关的事实至今无法查明,依据侵权法规定,医疗机构对病历如果存在着篡改、隐匿或者伪造,导致事实无法查清的,应直接认定医疗机构存在医疗过错,并承担赔偿责任。上诉人认为省医学会的鉴定依据不合法,没有依据。省医学会依据的是《内科学》第七版教科书,本案发生时各大医院正在使用,按照证据规则,教科书可以直接作为证据认定。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中,就,,医损(2012)140号医疗损害鉴定书,,,省人民医院申请,,省医学会专家出庭并就以下问题接受质询:第一、分析意见,第一段第二行BP220/250mmHg是否为本案的鉴定依据?第二、1月26日、27日两次急诊对于“上感”患者未检查记录生命体征(体温、血压等),该情况与患者死亡有无因果关系?第三、1月27日未使用抗生素与患者死亡有无因果关系?第四、患者于1月28日22:00出现神志模糊、胡言乱语,23:38医嘱发病重,1月29日8:06医嘱发病危,病重、病危医嘱已及时进行。分析说明4认为医方未及时报病重(病危),事实与规范依据何在?第五、2011年1月28日23:00病程记录记载:22:00患者出现神志模糊、胡言乱语,……,查体:BP105/70mmHg;内科护理记录单记载:1月28日22:00血压为106/78mmHg;被告认为,此两份记录是医护人员分别检测的即刻血压(入院后即予心电监护),此记录的形成是否附合临床常规。该事实是否与患者死亡存在因果关系?第六、鉴定分析说明,认为,医方几次讨论内容空洞,没有提出针对性的得力措施。医方认为讨论意见明确。所谓“得力措施”是否为根据治疗效果判断而得出的结论?本案中被告病例讨论应当得出哪些意见才符合规范?规范何在?第七、人民卫生出版社《内科学》第七版(2008年出版)第262页规定“高血压急症短时间内血压急骤下降,有可能使重要器官的血液灌注明显减少,应采取逐步控制性降压,即开始的24小时内降压降低20%-25%,24小时内血压不低于160/100mmHg”。医方降压过快可以导致多脏器损害。《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2005》、《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2010》中,就高血压急症的处理部分规定:在2-6h内将血压降至较安全水平,一般为160/100mmHg左右,在以后的24-48h逐步降低血压达到正常的水平。如以《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2005》、《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2010》为准,医方是否存在违规使用降压药并导致血压过快降低的情况?患者并非属于“高血压病伴脑卒中”,是否应当依照人民卫生出版社《内科学》第七版(2008年出版)第262页规定进行临床处理。第八、分析说明,认为医方存在的过错之一是“对于死因不明的病例,没有书面建议尸检”。医方认为,就尸检问题,现有法律规范没有规定一方有向患方告知的义务。医学会专家认定,医方就此存在过错的依据何在?有无进行书面告知并非技术问题,是否属于医疗损害鉴定的范畴?第九、分析说明中,“但本病例仍存在较多疑难复杂之处”,其中1认为,CT结果显梗塞病情并未进展。该意见是否表明,医方使用降血压药物并未导致其脑损害?第十、鉴定书中,列举了医方的“过错行为”及本案疑难复杂之处,但始终没有说明该过错行为与患者损害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及原因力大小,而是在分析说明及鉴定意见中直接认定“与患者死亡有一定因果关系”、“原因力大小为同等因素”,其认定的事实及科学依据何在? 鉴定人当庭接受质询并答复:第一:《医疗损害鉴定书》血压为220/250mmHg系笔误,专家组鉴定时血压读值为220/150mmHg。第二:“上呼吸道感染”不测体温,高血压急症(或亚急症)不测血压,对及时作出正确判断有影响,没有及时正确的诊断就不能及时地给予正确施治,影响患者的病程及预后,是医方的过错行为。第三:2011年1月26日,患者急诊时因血象高,使用了头孢匹胺2.0g,2011年1月27日再次就诊时未继续使用,单次使用抗菌素不符合治疗性(而非预防性使用)抗菌素使用规范,影响了对感染的控制,与患者不良预后有关。第四:患者2011年1月27日门诊已诊断为高血压病、高血压急症,但2011年1月28日9:22分,入住普通心脏病区后未发病重通知;2011年1月28日17:30分血钾2.94mmol/L(肌酐288umol/L)属危急值,医方仍未发病重通知;至2011年1月28日22:00(入院13小时),患者神志模糊,应答错误,出汗多,手足发麻,血压106/78mmHg于23:14发病重通知,2011年1月27日8:16分发病危通知,鉴定认为病情告知不及时、不充分。第五:2011年1月28日22:00护理记录血压106/78mmHg,脉率77次/分,呼吸30次/分,体温37.2℃,血糖14.0mmol/L,2011年1月28日23:00病程记录,血压105/70mmHg,心率76次/分,血糖14.0mmol/L,病程记录时间晚于护理记录,涵盖内容没有护理记录详细全面,只有血糖值吻合,故可以考虑血压和脉搏值尽管接近但可以是不同时间测得的。第六:参见第十条。第七:《中国高血压指南2010》,在处理高血压急症与亚急症的意见比较《内科学》更为详尽:高血压急症和高血压亚急症曾被称为高血压危象。高血压急症是指原发性或继发性高血压患者,在某些诱因作用下,血压突然和显著升高(一般超过180/120mmHg),同时伴有进行性心、脑、肾等重要靶器官功能不全的表现。高血压急症包括高血压脑病、颅内出血(脑出血和蛛网膜下腔出血)、脑梗死、急性心力衰竭、肺水肿、急性冠状动脉综合症(不稳定性心绞痛、急性非ST段抬高和ST段抬高心肌梗死)、主动脉夹层、痫等,应注意血压水平的高低与急性靶器官损害的程度并非呈正比。高血压亚急症是指血压显著升高但不伴靶器官损害。高血压急症需立即进行降压治疗以阻止靶器官进一步损害。在治疗前要明确用药种类、用药途径、血压目标水平和降压速度等。在临床应用时需考虑到药物的药理学和药代动力学作用对心排出量、全身血管阻力和靶器官灌注等血流动力学的影响,以及可能发生的不良反应。降压过程中要严密观察靶器官功能状况,如神经系统症状和体征的变化,胸痛是否加重等。由于已经存在靶器官的损害,过快或过度降压容易导致组织灌注压降低,诱发缺血事件。所以起始的降压目标并非使血压正常,而是渐进地将血压调控至不太高的水平,最大限度地防止或减轻心、脑、肾等靶器官损害。初始阶段(数分钟到1小时内)血压控制的目标为平均动脉压的降低幅度不超过治疗前水平的25%。在随后的2-6小时内将血压降至较安全水平,一般为160/100mmHg左右,如果可耐受这样的血压水平,临床情况稳定,在以后24-48小时逐步降低血压达到正常水平。降压时需充分考虑到患者的年龄、病程、血压升高的程度、靶器官损害和合并的临床状况,因人而异地制定具体的方案。对高血压亚急症患者,可在24-48小时将血压缓慢降至160/100mmHg。注意避免对某些无并发症但血压较高的患者进行过度治疗。在这些患者中静脉或大剂量口服负荷量降压药可产生不良反应或低血压,并可能造成相应损害。该患者入住心内科后3小时(2011年1月28日10:30分-2011年1月28日13:30分)静脉降压药使血压从190/110mmHg降至130/90mmHg,患者主诉头晕,后减量使用亚宁定至16:00,血压降至120/84mmHg,16:00后6小时一直未监测血压,至22:00患者神志模糊,胡言乱语,出汗多,时血压为106/78mmHg。就心内科11个半小时的治疗过程,参考《指南2010》,鉴定专家不会认为医方所采取的降压速度是合适的,降压目标设定是合适的,观察血压变化是密切的。患者由1月28日13:30出现头晕发展至1月18日22:00神志模糊,1月29日7:30意识丧失,与神经系统症状体征出现同时的血压值为130/90mmHg-106/78mmHg- 82/60mmHg,因此要考虑神经系统的症状体征是由脑部低灌注引起。第八:尸检问题:患者死因不清,双方持不同意见,在这种情况下,如医方向患者家属告知通过尸检能明确死亡原因,而尸检报告又恰恰能够证明多器官均存在组织、细胞的炎症、坏死反应,而非组织灌注不足的表现,那么,通过尸检就可以减少对死亡原因的分歧(尸检的意义及重要性恰恰在此)。第九:脑低灌注引起的梗塞通常为分水岭梗塞,该患者2次CT平均未见分水岭梗塞。然而,脑低灌注并非都引起分水岭脑梗塞,也就是说没有分水岭梗塞不能够否定脑低灌注的存在。临床应该结合降压过程中患者出现从头晕→神志模糊→昏迷的神经系统症状、体征的变化过程来判断存在脑部低灌注。第十:专家组鉴定中认为该案例的死亡原因不清,也可以说引起多脏器功能衰竭的病因不清,这正是该案例疑难复杂之处。1、2011年1月26日,患者因“咳嗽、咽痒3天”伴腰痛,耳鸣于2011年1月26日首先就诊(未测体温、血压),血象高,予头孢匹胺治疗。2、2011年1月27日,患者因“发热、心悸、气短、乏力”就诊,当时血压220/150mmHg,并有心电图异常改变(仍未测体温),经第二位医生检查诊断为“高血压病,高血压急症”,在门急诊予以相应处理。3、2011年1月28日,患者因“胸闷2月余,发现血压高2天”收住普通心脏内科病区,入院时神志清楚,体温37.5℃,脉搏99次/分,呼吸20次/分,血压180/100mmHg,肝颈静脉回流阴性,两肺呼吸音粗,右肺闻及干性啰音,心律齐,心率99次/分,肝脏肋下两横指,双下肢不肿,入院查中性粒细胞91.1%,肌酐288.8umol/L,血钾2.94mmol/L。入院诊断:1、高血压原因待查;2、肺部感染?3、多发性脑梗塞。据此既可以认为患者入院时就已存在的肾、心、肝脏器的损害是高血压急症时并存的靶器官损害;也可以考虑病原体感染(细菌?病毒?特殊病原体?)引起的多器官损害。要想明确原因进行尸检是最科学、有效的方法。没有尸检大体及病理生理报告,鉴定专家就会综合临床其他资料分析、判断、作出结论。患者入院先后接受了静脉、口服降压药物治疗,血压由1月28日13:30130/90mmHg,出现头晕;至1月28,22:00106/78mmHg,出现神志模糊;到1月29日7:3082/60mmHg,出现昏迷,脉氧84%。至此,医方开始给予升压、气管插管、呼吸机辅助呼吸、留置导尿等急救处置。于2011年1月29日10:17分转入老年ICU病房继续治疗,直至死亡。鉴定专家分析,患者神经系统症状体征的演变过程与血压降低及低血压有直接关系,故认为医疗过错行为与患者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如果能排除多器官功能衰竭的感染病因,医方的过错行为就不是同等因素的原因力,而是承担主要责任了。 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的陈述,病历资料、医药费票据、报销证明、两级医学会鉴定报告、,,省人民医院质询意见及,,省医学会书面意见等证据证实。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省医学会的鉴定意见是否应当予以采信,原审法院对赔偿责任比例的认定是否准确。 本院认为,医疗机构承担侵权赔偿责任的要件是其医疗行为存在过失且过失医疗行为与患者的损害后果之间有因果关系。在确认医方的医疗过失与患方的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的情况下,再依据医疗过失原因力的大小来确定医方承担赔偿责任的比例。 南京医学会医疗损害鉴定书认为,医方在对患者收住入院后对其综合病情认识不足,降压控制标准偏低,特别在患者1月28日22时出现意识障碍、血氧饱和度低后,处理措施欠积极,观察病情不全面,存在医疗过错。,,省医学会的鉴定意见认为,医方在治疗过程中,疏于观察,血压调整过快,早期对感染不够重视,未能及时调整治疗方案,与患者死亡有一定因果关系,认定医方存在的过错行为与患者死亡存在一定因果关系,其原因力大小为同等因素。两级医学会均指出医方在诊疗过程中存在过错,患者死亡与其自身存在多脏器功能损伤有关,但在患者自身存在高危因素情况下,医方对患者综合病情认识不足,未能及时调整治疗方案,与患者死亡有一定因果关系;两级医学会对医方降压控制均认为存在过错,,,省医学会认为根据《内科学》医方存在降压过快的过错,上诉人认为其适用的是《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2010》并据此要求重新鉴定,本院认为《内科学》、《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2010》本身在高血压防治上并不矛盾,但医疗活动是一种高度风险的活动,医方在诊疗过程中具体诊疗行为是否规范可能会危及到患者的生命健康安全,故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在医疗活动中,应严格遵守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诊疗护理规范、常规,从而最大限度的减少危及患者生命健康安全的可能性。两级医学会均认为医方降压控制过错与患者死亡有因果关系,一审法院结合两级医学会鉴定意见,医方在本案中存在的过错,同时考虑患者自身疾病的自然发展、变化,病人的个体差异及目前的医疗技术水平等原因,从而采信,,省医学会“医方存在的过错行为与患者死亡存在一定因果关系,其原因力大小为同等因素”的鉴定意见,并酌定医方在本次医疗损害中承担50%赔偿责任并无不当。上诉人主张按南京医学会鉴定意见承担相应责任同时要求重新鉴定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上诉人,,省人民医院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
网站公告
分析病历,预测判决,指导诉讼,只接医疗
分类
- 骨科
- 感染骨髓炎
- 钢板钢钉
- 骨折肌腱误诊
- 骨折后神经血管损伤
- 6
- 上肢和手
- 颈椎
- 胸椎腰椎
- 髋骨盆股骨头
- 膝关节
- 下肢
- 普外
- 甲状腺颈头
- 胸外和心脏
- 腹
- 肝胆
- 泌尿生殖
- 肛肠
- 感染
- 休克
- 麻醉
- 胎儿窘迫
- 产科
- 早产流产死胎
- 胎膜早破人工破膜
- 剖宫产子宫破裂
- 巨大儿
- 臂丛神经损伤
- 胎心监测
- 脑病脑瘫
- 444
- 产后大出血
- 瘘
- 出生畸形和超声
- 新生儿和儿科
- 妇科
- 计划生育
- 妇科肿瘤
- 40
- 心肌炎
- 心血管
- 心梗
- 介入
- 心脏手术
- 心衰
- 动脉夹层破裂
- 低钾高钾
- 肺栓塞
- 动脉静脉血栓
- 51
- 糖尿病和内分泌
- 内科
- 透析
- 诊所
- 过敏
- 120转院急诊
- 肿瘤
- 肿瘤误诊
- 化疗
- 放疗
- 肿瘤手术
- 眼科
- 牙科
- 耳鼻喉
- 中医针灸按摩
- 皮肤
- 美容
- 血液病
- 55
- 66
- 非法行医医疗事故罪
- 护理坠床
- 传染
- 协商投诉医调委
- 保险
- 辅助检查
- 病历
- 交通医疗事故
- 44
- 神经内科
- 脑梗塞
- 脑出血
- 脑介入
- 神经外科
- 脑瘤
- 颅内感染
- 脑脊液瘘
- 脑外伤
- 82
- 83
- 鉴定
- 诉讼
- 资料和指南
- 法律
- 音乐散文诗歌
网站文章
好友
暂时没有好友
友情链接
留言
- 暂时没有留言